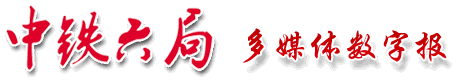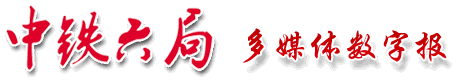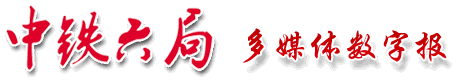北京今年的夏天比往年湿润,入夏的雨,来了又走,走了又来,淅淅沥沥下个不停。今天是立秋,清晨,我打开窗子,凉风扑面,深吸一口空气,沁人心脾,伸手窗外,晨熙伴着微风抚过手掌,清凉入心,足以让人欣喜不已。
假日,孩子总是比往日更早醒来,揉着朦胧的双眼站在你身旁,仿佛昨夜的残梦还没有从枕边溜走。第一缕秋风顺着窗沿吹进房间,吹在孩子身上,让她顿时清醒起来,放下双手静静地看着你。
走吧,让我们来一场秋日的旅行。当第二阵秋风吹进来时,孩子已经兴奋地跳起来。一家人匆匆吃了早饭,我整理好衣装,带着妻子和孩子,驾车直奔京城郊外,目标,潮白河东岸,东华山脚下,顺义——战友谭龙家。几乎每年的八月我都会去他家,为了和家人一起散散心,也是为了他家后面那方荷塘那片荷花。
车沿着北四环路向东行驶,孩子难掩出行的喜悦,问题不断,为了不扫她的兴致,妻子陪着玩耍,逗得她哈哈笑得合不拢嘴。进入顺义界,巨大的飞机轰鸣声从头顶滑过,孩子激动地看着天空,我特意将车窗放下,任由微风吹拂。驱车行走在潮白河大桥上,河里的水位比往年高很多,看着桥下翻滚的河水,颇为壮阔。桥真是奇妙的东西,它架在河的两岸,原为过渡而设,但是人们上了桥,却不急于赶赴对岸,反而耽赏风景起来,路边停了一长溜的车,人们站在车旁,拿着手机争相拍照。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,我们到了谭龙家,谭龙和他的爱人热情地招呼我们。
顺着小路,我们一边聊天,一边走向屋后的池塘,此时的阳光还不是很足,照在人身上,暖洋洋得让人发懒,两个孩子不顾这些,蹦蹦跳跳地在阳光下嬉闹,路上留下一串撒欢的脚印……
小路两旁的林子里不时传来知了的鸣叫,一阵风吹过,树叶哗哗作响,没走多久,我们便来到了池塘,这里应该不经常有人来过,两边满是杂草,里面的荷花却是千姿百态,有的花瓣全张开,连中间的小莲蓬也露出来,有的半开半闭,好像还有点难为情,还有的花苞包裹得很紧,就像插在水塘里的画笔。
然而,眼看着,芒种过了,大暑过了,立秋也来了,可是那方荷塘里的荷花仿佛从没有停止生长,它们在水中轻摇曼舞着,我的眼前晃动却尽是儿时家乡的影子……
我的家乡在河南,它位于黄河中下游,因处于九州之中,故有“中原”、“中州”之称。那里立秋时,水塘里满是盛开的荷花,荷叶与荷花挨挨挤挤,有白色、粉色,碧绿的荷叶承载着荷花,白色的花骨朵,真像一个个白白胖胖的娃娃。池塘周围种满了桃树、梨树、柿子树和核桃树,在微风中摇摇晃晃,树上不知名的鸟儿,叽叽喳喳地叫着,为初秋增添了几分热闹。
家乡的八月,是一叶的流浪,也是一朵花的招摇,水塘中的荷花似从《诗经》中走来,带着典籍的香韵,也似从《离骚》中走来,带着楚辞的意气,更像从祠堂中走来,带着祖辈的温度。它那亭亭玉立的身姿,盈盈抒情的美质,一会像窈窕淑女,一会又像翩翩君子,似田间的点缀,又如一个山村的涌动。
孩子们不知从哪里寻到一根长杆,拨弄着水塘里的荷叶,“这可不能!”谭龙忙制止了孩子们的鲁莽,“荷叶是青蛙嬉闹的歌台,是鱼儿避暑的凉伞,你看那一层层的绿浪,它在孕育着荷花的种子”。我们边聊边走着,仿佛只一溜,就溜到一天的末尾。七月流火,八月未央,在田间驻足,远处依旧是一望无垠的杂草,天上映照着洁白的云朵,叠映在孩子们的身影里。我看到树梢上淡淡涂上了一层金黄色,秋风吹斜了夕阳,告别了好友,踏上回家的行程。
八月七日,正值立秋,玉宇澄清,眺望远处,能见度极好,归途的黄昏中仿佛能看到天边的织女星与牵牛星。碰巧今年的七夕与立秋中间又相隔了七天,我心中盘算着,再过七天便是七夕,这段情愫千百年来引发了人们无数的情思与遐想,回望已经疲惫熟睡的女儿,心中暗暗祈求她的生活能安康和美好,七夕即将到来,这也许是人间最美的时节,真想待到来年秋风起,我还能乘着落叶载着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