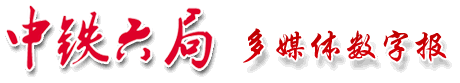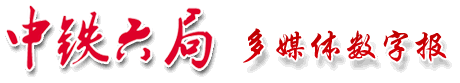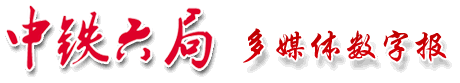娘酒,不仅是客家人的淳朴记忆,各种民俗文化的精髓,更是一份美丽的乡愁。
有客家人的地方,就必定有客家的娘酒。每当到其家里小坐,主人总会端上一碗黄酒:“渴了吧,来碗娘酒喝!”然后一碗米酒就会端到你的面前,黄澄澄弥漫着香气,那色泽与质感,就像乳汁中融入了几滴稠黄的蜂蜜,随着醇正的酒香飘入鼻中,顿时让人神清气爽。
《说文解字》对酒字的解释很有意思“酒,就也,所以就人性之善恶。”意思是说酒能成就人性之善恶,最终体现的还是人的一种品格,精神。
客家先民从北到南迁徙过程中,历尽苦难,饱经沧桑,陆续进入了江西赣江流域、闽西南和粤东北等地区,先民们南下路上衍生出了极为强烈的文化心理认同,在两宋期间,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山区少数民族特征的汉族民系。
客家人不断迁徙,离家越来越远的日子里,那种怅惘、孤独、寂寞,恋家情绪深重,郁结于心。离开家乡,还要走上多久,多远?在此,休憩片刻,喝上一口娘酒,那种烈性仗剑走天下的情绪被释放出来,朦胧、迷离的眼神中,远处一座座山峦,在秋风里蔓延,在酒水里发酵。
客家人的酿酒和饮酒方式已有1000多年历史了,秉承许多古中原地区的酒文化基因。起初酿酒时,客家人采用山楂树的根叶及自己种的高粱和小米来酿酒,后来采用制糖后的甘蔗渣酿酒,这种酒被称之为“滗酒”。到如今,客家人大都用糯米放入蒸笼,蒸成饭,加入酒饼和红菊发泡来酿酒。这种酒体呈暗黄色,所以客家人又称它为“客家黄酒”,也被当地人称为“娘酒”。
客家“娘酒”,还有一个十分温馨的故事。据相传中原汉人因避饥荒、战乱,大举南迁。一群人徒步越过千山万水,进入岭南的崇山峻岭之中,累得再也走不动了,一个个昏睡过去。后来被一长者所救,他用糯米酿成的酒让大家苏醒,补充了体力,又向大家传授酿造方法,之后扬长而去,这支中原的族人就在当地定居开拓,生息繁衍,客家娘酒也世代相传至今。
客家人常常说:“酿酒做豆腐,无人敢称老师傅。”客家地区家家户户几乎都精熟于酿制用糯米发酵而成的“客家娘酒”。因此,少不了酒瓮、酒缸,晒在庭前院后,逢年过节,妇女们在自家的灶头和院子里做娘酒。
蒸煮娘酒,颇讲究“土味”。娘酒的主要原料糯米,以刚脱壳的糙米为最好,水要用古井水,酒饼以江西、福建宁化的土酒饼为上,连清洗酒缸、酒瓮也不用洗洁精,而是用古井水清洗。糯米洗净后用大锅煮熟,接着把糯米饭放在箥簸里摊开,撒些有发酵作用的“酒饼”粉,用手搅拌,摊开凉透,待糯米饭凉了以后,倒进一个大水缸里,缸口用布或透明的蜡纸封住。
为了方便观察糯米发酵情况,封口时最好用透明的蜡纸,待闻到酒香时,大水缸里就会渗出一些发酵的娘酒。客家娘酒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将米酒从酒糟中过滤出来,装进小瓮中,加入红曲,用草皮封好,埋入燃有暗火的火堆中,炙酒完成后,把瓮口封起来,整个酿造过程就完成了,严谨的制作工艺,能保证酒质更加醇厚清香甜美,而且可以保留更长时间。
看着冒着气泡的酒缸,空气中弥漫着清新气息,感觉到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安静,没有多余情节,没有烦琐的过程,在那酒缸背后,我仿佛能感受到一种从容,一种自然,一次蜕变的过程,一次全新的升华。
这时,我似乎看到了酒中的一个个人影,一个个故事,在酒曲的融合下,像一粒粒洁白的糯米,被时间浸泡,膨胀、发软、融合,最终沉淀、积累、再造。醉人的芳香在空气中弥漫,久久不能挥去,娘酒醇香、爽口,喝到尽兴之时,酒意微微,脸上放光,五脏六腑似温水划过,热烘烘、暖融融,飘飘然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。
就这样,娘酒一点点地融入到客家人的生活,将酒倾倒在碗里、杯里,灌入水壶,背在身上,都不影响其味道的芬芳。客家的新生儿一出生,产房里就弥漫着酒香,坐月子的“娘”,都要喝上不少客家娘酒。孕妇生产后身体虚弱,必须进食一些补品,先把姜片放入客家娘酒煮沸,将鸡肉在锅里炒熟,放入沸腾的客家娘酒一起煮,鸡肉与娘酒一同烹饪,俗称鸡酒。于是,作为功臣们的母亲可以享受酒煮鸡,酒蒸蛋的待遇了。
客家儿女,哪个不是吃着母亲身上“娘酒煮鸡”化成的乳汁长大?谁能忘记母亲无私地付出和爱?“娘酒”就是乳汁,乳汁亦即是“娘酒”,哺育了客家千千万万的优秀儿女,难怪大家都说,娘酒是延续客家千年的血。千百年来,伴着先民们迁徙的脚步,娘酒就这样融入渗透进客家人的血脉,流淌在岁月与情感的醇香之中。
当地人称娘酒是思乡酒、母亲酒,在客家人的世界里,我看到的几乎都是妇女在做娘酒,如果没有勤劳的客家女人,娘酒就不能称其为娘酒了。客家女人们把米粒蒸煮成饭,再把饭酝酿成酒,酒成为男人们的钟爱之物,饱餐过后他们把气力又用在耕地上,播种成秧,结成稻穗,最后育成米粒,然后女人们又蒸煮化酒……周而复始,大道循环,千年一瞬,大地金黄。
酒水,凝结于一坛酒之中,无论走得多远,一壶米酒总能轻易唤醒那缕思乡的情结。远离故乡的日子,客家的娘酒就是我们心中那抹温暖的慰藉,就像临走时母亲的叮嘱,父亲手中那一杯送行酒,刻骨铭心,让我们慢慢啜饮,细细品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