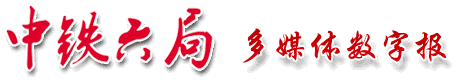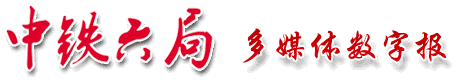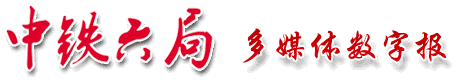自庚子年,疫情封城,传统木匠的生意就越来越少,即便如此,年近古稀的他们依然在街头坚守。
这两年木匠的活愈发难做,要么自备面包车,把后面的座位都卸掉,装上沙带砂盘机、气钉枪、手持电刨、圆形打磨机等等,把后备箱掀开来“等活”,木匠们搬张躺椅眯着眼睛,叼着五块钱一包的“大前门”吞云吐雾地等着雇主,整车的现代化工具在昏暗窄小的车厢里等着挑选。
要么就像眼前这个老头一样,背着一个老旧的绿色帆布包,包里有:锯子、净刨、墨斗、小方尺、打凿和鲁班尺等等。我更喜欢后者,帆布包里每一把工具,都带有传统木匠的印迹,也让人对木器更亲近。
真正接触过解木匠的人,你就会明白他们对事业的崇拜,“木头也是有灵魂的,干木匠活,只需眯了眼,拿上手里的工具,墨斗弹尺定线、小方尺定点、小孔手工打凿、粗坯用力净刨、露出细腻白白的木质就要用砂纸慢磨,木头与砂纸碰撞还会散发出一股特有的清香味。”父亲说起木头就像孩子一样,能喋喋不休聊很久。
父亲说建房、锯木是一件苦事。每逢雨季,对于木匠来说就是一道坎儿,木头不能碰水,雨水一泡就烂,遇到乌云压顶,他就像突击队员一样,迅速地用塑料布、尼龙袋、大遮阳伞,将木头严严实实地盖上,用绳子封紧,生怕被水沾湿。
盛夏的雨通常都来得十分迅猛,刚才还是晴空万里,不一会工夫天上乌云密布,眼看雨就要下起来,木头还没有盖完,雨鞭子已经抽打下来,雨水浇在头发上、抽打在脸上,湿透了全身,大雨过后,穿着湿漉漉的衣服还要继续锯木。父亲说:“为了生活,咬牙也要坚持”。
上个世纪的农村,谁家有婚嫁喜事,都会请木匠到家中打几套嫁妆,谁家缺什么家具,也会请木匠来打桌子、凳子等家什,那时的木匠生意非常红火。然而,随着时代变迁,曾经从木匠手中制作出来的家具,已经被现代化工厂的生产线所取代,曾经挑着工具走村串户的父亲,也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。
家中有一处是父亲专门摆放工具的地方,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拿出来擦拭上油,保存得非常好。他以前去雇主家做工,木料都是自己用双肩扛着去,姜黄色的无袖背心一次又一次被汗水洇湿,汗渍周围,结了一层薄薄的、硬硬的盐霜,遇上好心的雇主,进门后会给一瓶饮料,父亲总是偷偷留下来放进帆布包留给我们喝。有的酸、有的甜、还有的苦,苦得能呛人流眼泪。
高中毕业,父亲带我进城,遇到街坊他便会说:“我女儿,今年刚考上大学,以前只知闷头读书,外头的人情世故都不懂,带她出来走走,补上这一课。”有熟人问孩子大学读什么专业,他说:“她自己要念设计,以后带我住她设计的大房子”。
那时我从“埋头读书”的状态中,一下子被推进了五光十色的市井生活,就像一个没有准备好的发言人被推到讲台上,有点力不从心。跟着父亲墨斗弹线、角尺度量、斗拱拼装,都慢上一拍,当父亲的,常会半是嗔怪半是怜爱地对着我低沉地轻声呵斥,像鞭策,又像勉励。父亲说:“墨斗装知识、小方尺定方向、打凿练耐心、鲁班尺能丈量人生”。
总之,那次是父亲几十年来做的最扬眉吐气的一次活,我能很明显地感受到,他是那种牵挂和不舍,跟着他一个月,皮肤晒得黢黑,拿着雇主给的百元大钞,我去千里之外上大学了。走的时候父亲送了我一根“山城牌”八角木工铅笔,他说:“娃子,好好学习,铅笔写错了能改,人生一旦错了就无法改正了”。
辛丑年,疫情解封,传统木匠的生意开始回春,我回老家接父亲进城,眼前这个花甲之年的老头,依旧背着一个老旧的绿色帆布包,包里有,锯子、净刨、墨斗、小方尺、打凿和鲁班尺,坐在木匠市场等活。我下班后到木匠市场接父亲“咱歇了吧!”父亲露出一丝丰收后的疲倦和淡淡的寂寞说:“走,回家”。